《传统中国能动司法研究》2020年出版
图:封面、版权页、目录
文:内容简介,序(范忠信教授),自序,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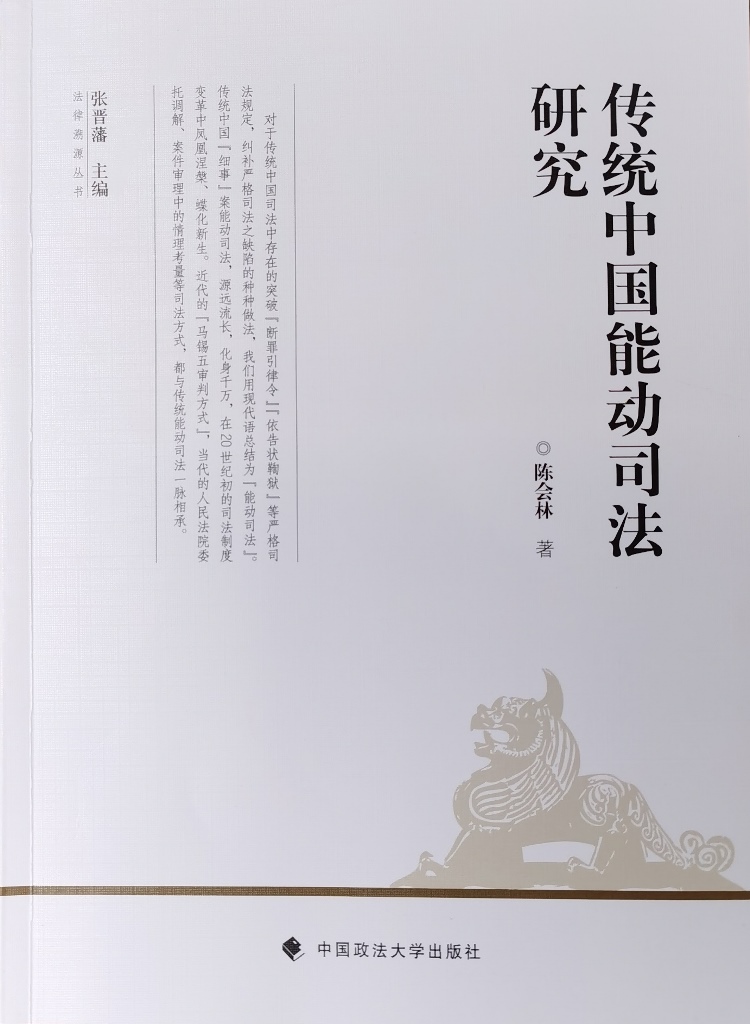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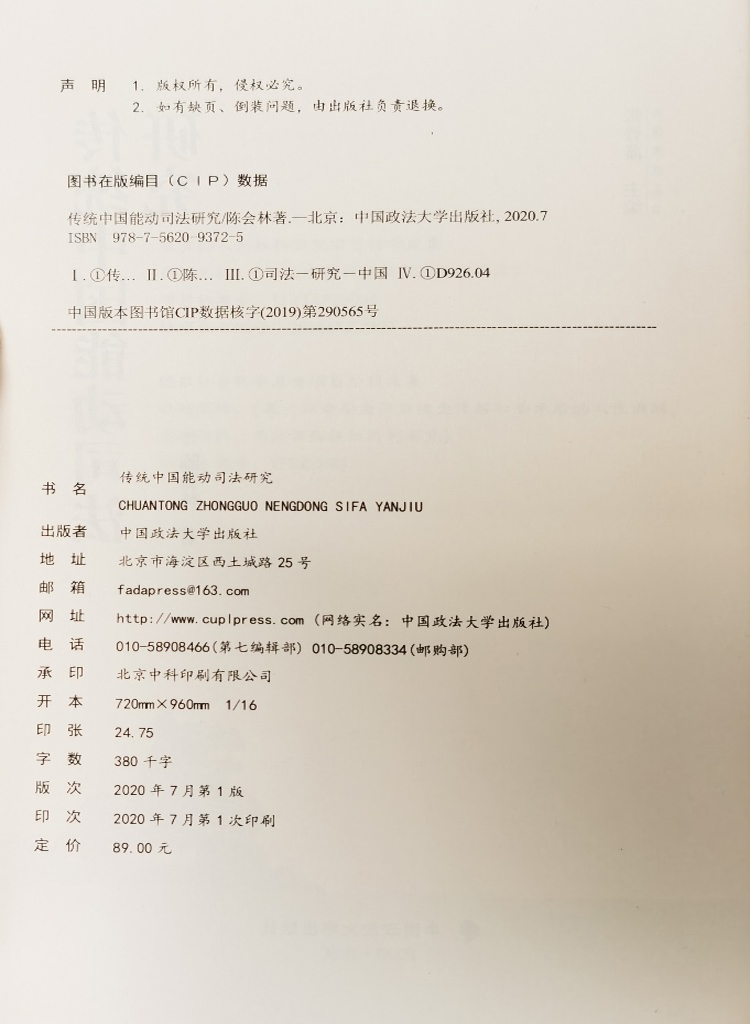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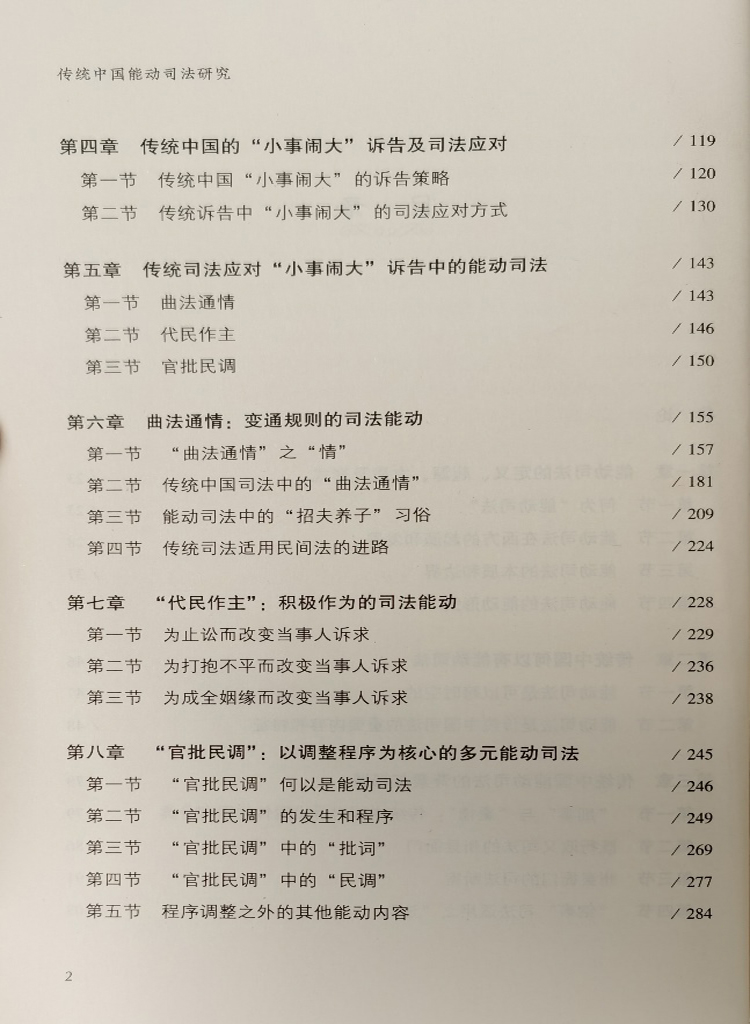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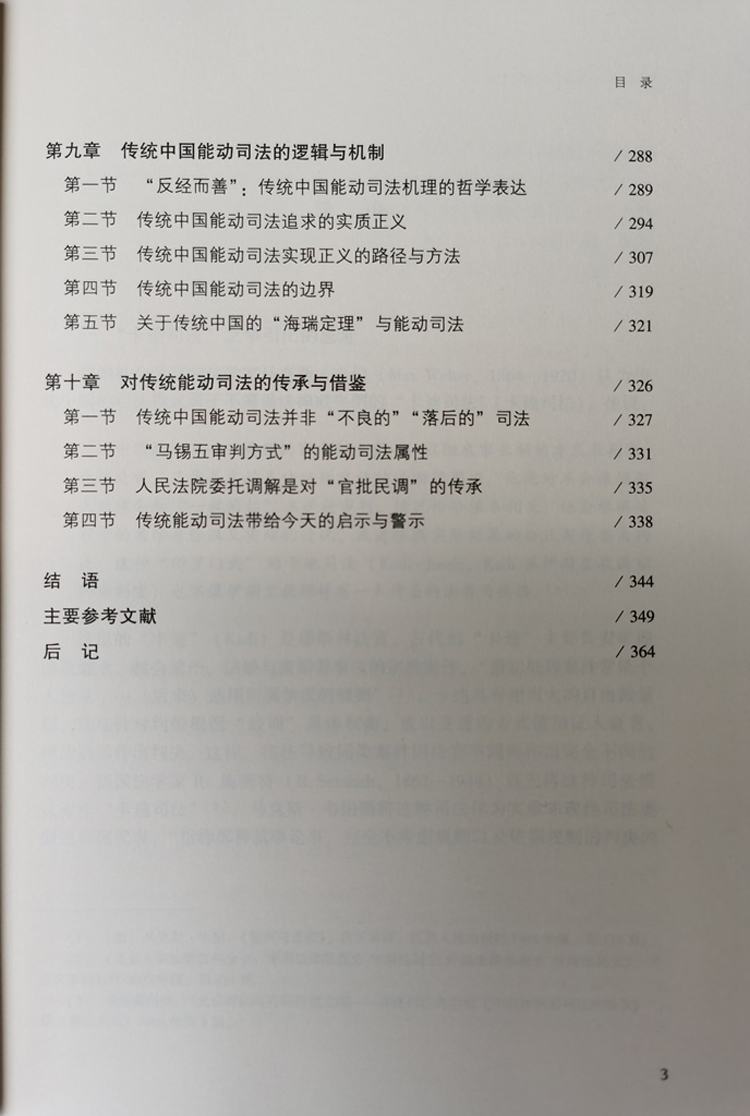
“能动司法”(judicial activism)的固有表达源自美国。“能动司法”作为一种司法模式或司法理念,历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我国2009年前后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语境下,司法界对“能动司法”进行了运动式的倡导、探索和实践,并且形成当代中国可以有、甚至必须有“能动司法”的主流观点或认识,但是对于传统中国有没有能动司法的问题,学界缺乏应有的关注。
对于传统中国司法中存在的、突破“断罪引律令”(这里的“罪”即不法行为)“依告状鞫狱”等严格司法规定,纠补严格司法之缺陷的种种做法,我们用现代语言总结并表达为“能动司法”。本著在中西贯通语境下,从能动司法的视角考察和解读传统中国“细事”(民事性)案件审理的规则或程序往往并不严格依据“国法”,乃至有所谓“卡迪”司法嫌疑的法律现象。“能动司法”是语源来自西方,但在国内外都曾大行其道的特别司法模式。这里的能动司法是指司法机关或司法官在特殊案件审理过程中,在法治前提下,积极作为、变通规则、调整程序、扩张功能,最大限度实现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和司法方式。传统中国没有“能动司法”的这一术语的固有表达,但普遍存在能动司法的事实。传统中国能动司法的主流反映了古今共通的某些司法规律和法律智慧。
本著的考察和研究,以特别能反映传统中国司法规律与特质的、司法应对“小事闹大”诉告的策略为切入点,以司法经验较为成熟、研究史料相对丰富的清代为重点时间段。本著认为,传统中国“细事”能动司法的方式主要有三大类:变通规则的“曲法通情”、积极作为的“代民作主”、调整程序的“官批民调”;“反经而善”可以反映传统中国能动司法的哲学机理;传统中国的能动司法主要以“定分止争”为基本路径和方法、以不违“天理”和不徇私情为边界、以“和睦”为实质正义追求的终极标准;强调人伦、追求和睦是传统中国能动司法不同于西方能动司法的根本特征,传统中国能动司法是一种“情理教化息讼”型能动司法。
传统中国“细事”能动司法,源远流长,化身千万,至20世纪初在近代民事司法变革中凤凰涅槃、蝶化新生。近代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当代的人民法院委托调解、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司法方式都与传统能动司法一脉相承。当下中国的能动司法并非完全是创新。
传统能动司法与现代能动司法,不完全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因为两者各有其特定的社会生态与政治基础,但两者意气相通,其共通的思想元素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相对而言,如果说在农耕文明、宗法社会、熟人社会、非民主非法治的传统中国,能动司法追求以“和睦”为主要标准的实质正义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话,那么在工商文明、公民社会、生人社会、追求民主法治的现代中国,能动司法追求的实质正义,就应该主要是维护和保障权利,通过“维权”实现“维稳”。
本书的研究,既有学术视野,又有现实情怀。为了能使本书“惠及”实务界,本书没有刻意省略那些在法律史专家们看来是“常识”,但删掉它们则可能影响实务人士完整理解的内容,以致本书说了不少“正确的废话”。
本著的研究,试图初步建构起一套较为合理的传统中国能动司法话语体系,并以此总结传统司法的相关经验和智慧,推进对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特色的认识,为当代中国司法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传统本土资源,为“东方法律主义”的可能性和适度的文化自信提供历史佐证。
范忠信·序
会林这部专论传统中国“能动司法”问题的著作,视角特殊,思路新颖。粗览一遍,获得启发不少。关于吾国司法之“情理法兼顾”传统,多年前我曾稍有涉足,虽然尚未名之以“能动司法”,但初有一些感悟。会林将这一研究推向更高境界,发我所未言,履我所未及,令人欣慰。欣悦之余,将读后感想串联起来,权充序言,权作荐语。
这本书,据我所知,是关于传统中国“能动司法”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是第一部从“能动司法”视角全面研究传统中国司法模式的论著。说它是第一部,决不是说此前没有任何研究著述涉及这一问题,而是强调本书是以“能动司法”一语概括传统司法之“情理法兼顾”特性并系统深入探究的第一部著作。
会林的这一研究,大约始于2008年。是年他开始做国家司法与民间解纷联接问题的研究,获司法部法学研究基金立项支持。从这一课题出发,会林顺势将传统中国官民互动解纷问题的研究延伸到对“情理法兼顾”即注重“权变”或“权宜”这一传统司法特性的研究,长期思考至今,难能可贵。尤其是,2011年夏,《传统中国的能动司法模式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资助后,会林的这一研究更如拓黑土,如种嘉禾,收获颇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部著作,就是他十年思索、“十年磨一剑”的结果。
“能动司法”的概念或提法,古代中国当然没有,但不能因此说古代中国没有能动司法的实践。突破现行成文法的某些硬性规则,在具体案件审理中,结合天理人情,结合风俗习惯,作出“权宜”或“权变”的司法调处或裁判,这种做法当然就是今人所谓“能动司法”。会林在书中集中讨论的那些做法,如“突破‘断罪引律令’、‘依告状鞫狱’等严格司法规定,从而纠补其缺陷的种种做法”,其实就是古时的能动司法。这种“能动司法”,不仅在“细事”(“自理词讼”案)中比较普遍,而且在“重情”(“命盗狱讼”案)中也大量存在。这是传统中国司法不同于近现代司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会林对这一方面进行的探讨,超越了过去“情理法兼顾”问题研究视野,触及传统司法的权变(权宜)模式及其价值判断选择艺术问题,这是值得注意的。更可贵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会林特别强调了两个前提:一是强调能动司法所突破的“法”,主要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亦即通常所说的“国法”,并不是广义上的法;二是强调能动司法之“变通”或“权宜”是在那时人们公认的正义价值准则指导下,以天理人情即中国式自然法为旨归,并非漫无标准。他认识到这种能动司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有时允许在遵循法治原则前提下积极作为、变通规则、调整程序、扩张功能,最大限度实观公平正义的“司法能动主义”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会林的这一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启发尤多。
第一,从能动司法视角研究传统中国司法模式,有助于深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是司法文化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传统中国司法的价值宗旨及解纷技巧。因为所谓能动,绝不是乱动,而是绕过成文法中的障碍回复伦理价值的断狱决讼艺术。紧扣目标、巧避障碍二者是一物两面不可分开。这样的司法艺术,当然不是“卡迪司法”一语所能概括。对这样司法艺术的全面研究,其所注重的当然不是一般的解纷技巧,而是克服困难恢复正义价值或秩序的技巧。从能动司法视角研究这一技巧,当然更可能深入解读中国传统司法的民族个性或民族风格。
第二,从对民间“小事闹大”诉告策略的官方司法应对技巧的考察出发,会林系统梳理了传统中国州县衙门在断理“细事”(词讼)案时的能动司法情形,总结分析了其中的一些有共性的特征或规律,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他将官府在“细事”审理中的司法能动归纳为三类,即变通规则的“曲法通情”,积极作为的“代民作主”,调整程序的“官批民调”等,这种分类分析和总结,当然更好地揭示了传统司法的内在规律。特别是,会林借汉人赵岐“反经而善”一语概括传统中国能动司法的哲学宗旨,揭示了能动司法表面虽违反常法而实际上更合乎法上之法(善或正义)的本质属性,这确实是切中肯綮之论。
第三,从与今日能动司法追求的差异视角去考察分析传统中国能动司法的特性,这一方面更予人重要启发。会林注意到,传统中国的能动司法,有很多不同于今日司法能动追求之处。他提醒我们注意,在传统中国的能动司法操作中,重和谐轻权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和谐与权利对立起来)、重教化轻审断、重情理轻国法、父权家长式息讼、审判与行政职能不分等等,几乎如魂随躯。但他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这几条就给传统中国能动司法简单扣上“不良”或“落后”帽子。古今中国的社会生活生态不同、政治法律秩序不同,我们不可用今人的价值标准去苛求古人司法,而应该看到这一模式在降低司法成本、保护正当权益、恢复社会和谐等方面的永恒意义。会林注意从中西会通视角乃至所谓“法律东方主义”语境中讨论这一问题,更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四,对中华法系的一些不同于其它法系的特征进行新的分析阐发,会林也颇有心得。他认为,传统中国“法”的内质主要是“刑”,是惩罚违反“礼”、不服从君王号令、不响应圣贤感召、轻肇事端轻启纷争等行为的刑罚制裁规范;古人并没有关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分类的意识,认为所有不当行为都是“罪”或“恶”,都可以施以轻重不等的刑罚,于是历代律典更多看起来“长”得都像“刑法”,令、科、格、式、例等都是“刑法”的衍生物或为“刑法”服务的;因为坚持“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治理逻辑,所以法律体系没有也无需像今天这样复杂和完善(所谓“法网恢恢”),“天理”“人情”之类的非“法”(国法)规则必然更多地进入司法领域;在司法上没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之类的严格分别,只有根据“罪”情轻重的“细事”与“重情”(“词讼”与“狱讼”)的分别;旧时律典强调的“断罪引律令”规则,与今天的“罪刑法定”追求也不完全是一回事,等等。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新意。
在本书中,会林想为传统中国司法的“能动司法”方面特征建构起一套重述话语体系,这种努力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初有成效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主观客观限制,本书的研究离这套话语体系的完成还有相当距离,“细事”案能动司法模式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化,“重情”案能动司法模式研究有待正式开始,古时能动司法模式与今日司法能动主义追求的内在价值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分析阐发有待深入,这是我们可以继续期待于会林的,也是他未来研究可能继续格外着力之处。
匆匆阅读并草记感悟,疑未全面深入理解。井视管窥,勉强为序。
范忠信
2019年5月3日于余杭古镇凤凰山北麓参赞居
“近代以前,中国一直稳健地走着自己的路”[①],以至可以说中华文明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之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博大而精深,垂世而独立,其重要表现之一便是传统中国的法制模式与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德主刑(法)辅”的规范结构、人际和睦与社会和谐的目的追求等方面所表现的不同于西方的“路向”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西方美国著名学者、当代“头号中国通”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说:
(传统)中国的法律概念根本不同于西方。它起源于古代中国人对天理(自然秩序)的观念,认为人的行动必须合乎天理,而统治者的职责是维护这种协调一致。统治者是以懿行美德而不以法律来影响百姓的,所以认为通晓事理的文明人会受这种榜样和高尚行为规范的指引,而毋需绳以法规。按照这一理论,只有对那些野蛮的、未开化的人,即那些不遵圣贤教导和皇帝榜样的人,才需要实行惩罚而使其愉服。明正赏罚,在于表明每个人按其身分应采取什么样的合乎体统的行动。但在理论上,赏罚总被认为是保证人们循规蹈距的次要手段,其目的是“以罚止罚”。[②]
这是说传统中国的法(国法)主要是用来制裁那些破坏人际和睦、社会和谐,尤其是“不遵圣贤教导和皇帝榜样”的人的工具,而不是近现代意义上规定权利义务的法律。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1921-2008)说:“纵观世界历史,可说欧洲的法文化本身是极具独特性的。而与此相对,持有完全不同且最有对极性的法文化的历史社会似乎就是中国了。”[③]王亚新教授讲:“传统中国的法与审判可以说是人们从另一个方向上设想和构筑秩序并将其发展到极为成熟精致高度的产物,是另一种同样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人类文明的体现。”[④]
纵然,中西传统法律文化,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法制模式,但并非像滋贺秀三所说的“完全不同”[⑤],例如在传统中国的司法方面,费正清评论道:
一般说来,法律在国内既不是首要的,也不是遍及一切的,而且人们觉得,如果像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夏洛克那样援引法律条文,那就是不顾真正的道德,或者承认自己的讼案有亏德行。要做到公允,执法必须衡情度理。[⑥]
梁治平教授说:“时人多以为西人行事严格地依据法条,吾人行事则散漫无章,仅有抽象的道德原则或模糊的公正观念作指导。这两种看法同样地似是而非。……大而言之,经与权乃是所有受规则支配的人类共同的问题。吾人与西人的差别,在这一种意义上,只有程度的不同。”[⑦]能动司法就是中西法制“同曲异工”“殊途同归”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对于“严格司法”而言的“能动司法”,是司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经”(法定规则、程序等)进行“权”(灵活变通),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和司法方式。
中华法系具有很多能动司法的条件和元素。近代著名法学家陈顾远先生(1896-1981)在《中国固有法系之简要造像》一文中将中华法系的特色概括为六个方面:“神采为人文主义,并具有自然法像之意念”;“资质为义务本位,并且有社会本位之色彩”;“容貌为礼教中心,并具有仁道恕道之光芒”;“筋脉为家族观念,并具有尊卑歧视之情景”;“胸襟为弭讼至上,并且有扶弱抑强之设想”;“心愿为审断负责,并且有灵活运用之倾向”。这里“灵活运用”之“心愿”,说的就是能动司法问题。所谓“(司法官)在刑狱方面适应时代环境之需要,自不必拘守一格,极尽其灵活之运用……一方面尊重法律之安定性,一方面抬高法律之适应性,并非一成不变者可知”。而“仁道恕道”之“容貌”“扶弱抑强”之“胸襟”,都是中华法系追求的实质正义的特有内容,也与能动司法相关。[⑧]
传统中国司法有道德化、行政化与非专门化(非职业化)、人情化与艺术化、个别化和非逻辑化等特质[⑨],这些特质的一个重要共性就是“能动性”。正如陈景良教授所指出的:“在古代中国的‘礼法传统’下,法官审理案件首先是依法判决是非,其次是援情入法,尤其是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审理者不能单独地、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而是要特别注意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间的平衡。审判既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也是儒家追求‘和谐’,倡导‘致中和’精神的实现。”[⑩]在特定案件的审理中,司法官“曲法通情”“代民作主”“官批民调”等做法,在今天或许出人意料,但在古时则理所当然。能动司法是传统中国司法的一道靓丽风景,反映了先贤们的司法艺术和法律智慧。
关于传统中国法制的研究,瞿同祖(1910-2008)先生曾警示我们要注意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差异,他说:“研究法律自然离不开条文的分析,这是研究的根据。但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意实施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11]有学者对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主要是民事性判例集)所收470余件书判的判决依据情况进行统计后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绝大多数判决并未引述“国法”条文,直接引述法条的书判仅115件,不到四分之一。第二,未引法条或法意未详、书面上明显以其他理由作为主要判决依据的,至少有67例。第三,有些判决即使明确引述“国法”规定,但仍以各种理由进行“权断”,这类书判至少有33例。[12]从这里的研究结果来看,南宋民事性司法审判中普遍存在着“曲法通情”的能动司法情形,这实际上是传统中国司法的一个缩影。
“反经而善”[13]“通变达理”“反常而合于道”[14]等等表述,是中国先贤对“特殊情况下灵活变通运用常经或常规才可实现真善或道义(实质正义)”这样一种意思的固有表达。这类表达虽然不是直接针对能动司法的,但它是“传统中国司法通过能动司法实现实质正义”的较好表示,完全可以用来表达传统中国能动司法的精义和神韵。
任何研究都是基于特定的语境或理论基础而展开的。本书探讨能动司法在传统中国的存在及表现、机理和意义,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或争议性的话题,这个话题主要基于以下理论预设或逻辑前提:
1.本著所谓“能动司法”是司法机关或司法官在特殊案件审理过程中,在法治前提下,积极作为、变通规则、调整程序、扩张功能,最大限度实现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和司法方式,这一定义不同于其语源故乡美国早期基于司法审查的司法能动主义,但与美国现代司法能动主义形神相通。这样界定“能动司法”,表明我们建立自我话语体系的努力,同时也表明我们记取苏力教授对我们的警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不能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这样弄不好只会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中,从而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的工具”[15]。能动司法的定义是本著所有内容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
2.传统中国没有“能动司法”的说法,但有能动司法的做法,其能动形式主要有变通规则的“曲法通情”、积极作为的“代民作主”、调整程序的“官批民调”等。传统中国对司法功能的认知有儒家的“和为贵”、法家的“定分止争”等固有表达,通过“定分止争”实现“和为贵”大概是传统中国能动司法发生的逻辑场域。传统中国的能动司法主要发生于严格司法不利于实现实质正义(例如人际和睦)时的情形,并非说传统中国所有司法都是能动的。
3.能动司法之“法”是“正式的和公共的法律”,亦即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其在传统中国主要是“国法”,包括律、礼、令、例、典等形式,不包括“天理”和“人情”。
4.“细事”“细故”和“重情”“重案”是传统中国对案件的重要分类,本书勉强将它们分别对应于今天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传统中国没有部门法的概念或思维,没有今天民事、刑事等分类,其法律观念中只有根据违法轻重施以不同处罚的思维,所有违法行为都是“罪”,所有处罚都是“刑”,轻罪(细事案)处笞杖刑,重罪(重案)处徒流死刑。古代的罪不是今天的罪,古代的“刑”不是现在“刑法”的“刑”,笞、杖、徒、流、死等处罚在今天看来都是“刑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清大理院正卿张仁黼(?-1908)才说:“中国(古代)法律,惟刑法一种,而户婚、田土事项,亦列入刑法之中,是法律既不完备,而刑法与民法不分”[16]。但传统中国“轻罪”(笞杖刑案件)与“重罪”(徒流刑案件)之类的区分还是有的,大致来说,前者可对应于民事案件,后者可对应于刑事案件。今天说传统中国法有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只是将有关内容与今天的部门法大致比附对应,是“以今观古”的体现。
5.本书主要探讨针对“细事”案的能动司法,但实际上传统中国的“重案”司法也存在能动的情形。[17]今天的刑事司法要求严格遵行“罪刑法定”原则,不允许能动司法,传统中国的“重案”司法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刑事司法。
基于农耕、宗法、帝制的司法文明,整体上不适于今天追求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工商文明社会,但其中有些可以贯通古今的司法规律和法律智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本书用现代法理考量传统司法,对传统中国司法中的能动情形进行考察和解读,试图初步建构一套较为合理的传统能动司法话语体系,为当代中国司法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传统本土资源,为“东方法律主义”的可能性和我们适度的文化自信提供历史佐证因素。
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只有在现代语境和全球背景中才能彰显其特色,昭示其意义。本著的讨论注重从现代和全球两个视角建构传统中国能动司法的话语体系。
就现代视角来说,传统法律文化可以在纵向比较中得到理性评判和价值定位。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先生讲:“贯穿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乃是中国法律研究今后所应该走的方向。唯有如此,才可能建立既有历史的特殊性也有普适性的,并具有实用意义的中国现代法律。”[18]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代中国的法学是随着法律移植建立起来的,与固有传统形成某种程度的断裂,“我国的现代法学不同于许多中国传统的人文学科,后者有一个相当久的传统,有自己的命题、范畴、概念和语汇;目前的中国法学则不同,它的几乎全部范畴、命题和体系包括术语都是20世纪以后才从国外进口的,与中国传统和现实有较大的差距”。[19]现实是研究传统应有的基本面向。毕竟,在某种意义上,“理论是实践的眼睛。”[20]
就全球视角来说,传统法律文化可以在横向比较中获得独立价值和普世意义。“19世纪至今,中国完全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广阔图景之中,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法的研究便不能不参照世界其他法律的发展”[21];“与作为对照实例的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可望深化人们对于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思想意识的不同类型以及规范秩序的不同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理解。”[22]相对而言,对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全球性”把握比较复杂和麻烦,“自近代以来整个法律体系以西方法为导向的全面转型,导致我们今天在理解传统中国的法观念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23]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研究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这样弄不好只会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中,从而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的工具”。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本土化还具有它自己的意义……不满足于只能被表现,而是要自我表现”,[24]也就是说,不管是用民族语言,还是用外来思想,传统法文化研究总要建立自已的话语体系。
传统中国能动司法问题的讨论,是基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法制比较语境展开的,在东西方法律文化比较和东方法律文化特质的认知方面,西方学界有所谓“法律东方主义”(Legal Orientalism)和“东方法律主义”(Oriental Legalism)的表达,这套话语在西方影响很大,近年来也被国内很多学者关注和讨论。能动司法的问题(《法律东方主义》一书的讨论正是从司法问题切入的)是考察(或参与讨论)“法律东方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或切入点。下面就相关问题谈点粗浅认识[25],以示我们理解传统中国能动司法的多重视角。
迄今为止,有关“法律东方主义”的代表作主要是两位美国学者的著作: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又译为“东方主义”)[26]和络德睦(Teemu Ruskola)2013年出版的《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化》[27],这两本书“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28],此即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或对立。在后著中,作者明确提出了“法律东方主义”和“东方法律主义”的概念[29]。
所谓“法律东方主义”,按络德睦教授的说法,“乃是一套关于何谓无法以及何人并不拥有法的未被言明的文化预设……(因为)如果缺乏一种无法的、专制的东方作为陪衬,那么一个法律现代性的世界也就不会存在”[30],其所要表达的核心意思,依笔者的理解,大致是说中国法制因为没有西方(主要是美国)法制所拥有的那些特质——规范方面直接规定权利义务、区分公法与私法(有部门法意义上的民法),司法方面遵从法律至上主义(不是法律工具主义)——而实际上是一种“无法”的法律制度,“法律东方主义”就是西方“有法主义”映衬下的东方“无法主义”。[31]显然,法律东方主义是西方人揶揄东方法律文化、确认西方法律优越性的一套“法律文明等级论”叙事。
所谓“东方法律主义”,似乎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对中国法律文化的理解,亦即认为中国法律文化如果用西方标准判断,就是“法律东方主义”;如果用东方标准判断,就是“东方法律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络德睦教授《法律东方主义》一书最后部分提出“法律东方主义抑或东方法律主义”[32]的疑问。二是制度建设意义上的,对中国法制发展之“有法”的预期或期待。这方面如果说络德睦教授说得较为“模棱两可”——中国法制发展要么是步趋欧美,要么“独树一帜”,“或许总有一天中国将会屈从于现代欧美形式的法治,从而确认其普世性,或者它将会采用一种正在演进中的中国普世主义(一种东方法律主义)形式重塑法治”[33],那么《法律东方主义》一书的中文译者、魏磊杰博士说的则较为明确:“(东方法律主义)就是重新建构一种新的理解法律与法治的话语与观念,唤醒东方,使得东方重新获得它的主体性,重新变成一个有法的主体,以此作为克服和超越法律东方主义的一种可能的途径”[34],这个意义上的“东方法律主义”是对“法律东方主义”的超越,但这种“东方法律主义”仍在路上。
西方在东方文化认识问题上的殖民主义色彩逐步褪去,例如络德睦教授说:“法律是当代世界政治本体论的关键层面。……如果不考虑中国在其间的位置,那么就无法完全理解当今世界”[35],但“法律东方主义”和“东方法律主义”都是西方人基于西方标杆或“在法治与人治之间进行一种准神学的对比”(络德睦语)而建构的概念或话语,是欧美人眼中“非我族类”[36]的产物。
笔者在这里无意、也无力对“法律东方主义”问题作出全面评判,仅对作为一种符号性公共话语的“法律东方主义”在思维方式或逻辑层面上可能存在的问题,说点个人看法。这里的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以西方标准取代“普世标准”有失公允。试想,如果我们把“法”定义为“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这也是本书对“法”的基本定义)之类,而不是刻意强调法律直接规定权利义务,可能就无所谓法律的“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之争。更何况德国法学家茨威格特(K. Zweigert)和克茨(H.Kotz)说过,“每个社会的法律实质上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极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37]
第二,将中国古代帝制时期的法律文化与西方近代民主时期的法律文化进行“错位”比较是不科学的。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主要是在中国帝制时期和美国近现代民主时期的法制比较语境中论说“法律东方主义”的,帝制中国与民主美国,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各自有着不同的社会生态(例如中国是农耕文明、宗法社会,美国是工商文明、公民社会)。我们不能要求北方的土地上也长出椰子树来。法律制度不是空中楼阁,在很大程度上,什么样的社会生态便长出什么样的法制[38],这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也有相当的共识,例如霍姆斯(1841-1935年)就说:“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其运作,其实际内容就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当时人们理解的便利。”[39]对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法制进行“事实描述”,乃至以“特色”或“主义”进行区别是可以的,但如果借“特色”或“主义”之名作出落后与进步的结论或价值判断则是伪命题或伪判断,否则,我们就便可以针对美国发明电脑而说中国人发明算盘是“科技东方主义”,是落后的东西。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中国旧法制是‘非现代’的,然而按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还不应马上称它是‘落后’的。早期欧洲观察者曾对中国人的秉公执法获有深刻印象。只是到了18、19世纪,西方改革了法律和刑律之后,中国才落后了。”[40]台湾学者黄源盛教授说:“从比较法史的角度观察,传统中国自有法,是为‘家族伦理法’;西方近代自有法,是为‘个人权利法',各自有其产生的时空社会背景,这无关乎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41]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将欧美和传统中国的诉讼类型分别称之为“竞技性诉讼”和“父母官诉讼”,认为“这两种诉讼类型由根本理念的不同而形成如此的区别。两者各自都有其长处和弱点,不能说哪一方是蒙昧和落后的。这正是文化的差异。只是从父母官型诉讼中产生不出jus、Recht系列的概念来,这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种宿命。”[42]
话说回来,尽管传统中国与近代美国的能动司法有很多差异,但总归来说,“司法能动现象”是东西方法制的重要相同共通之处。说“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43]也好,说从“法律东方主义”迈向“东方法律主义”[44]也好,本著都想做出自己的努力,此尝试在统一话语体系中诠释传统中国的能动司法。
德国思想家和诗人歌德(1749-1832)说:“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45]本著的研究正是一种“重新思考”——从能动司法的特定视角对传统中国司法特质的再思考再研究。“旧视角”的同类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例如著顾元教授的《衡平司法与中国传统法律秩序》[46]、刘军平博士的《中国传统诉讼之”情判“研究》[47],以及范忠信教授的《情理法与中国人》[48]、梁治平教授的《法意与人情》[49],等等。本书可能没有实质性的理论创新。如果说“新视角”除了“可以把不能解决的问题转化为自己有能力解决的问题”[50]之外,还有助于深化对现有材料和既有问题的认识,那么新视角也可以忝列创新。
本著的“重新思考”试图在“还原历史”和“升华意义”两个维度或目标上努力,这大概就是达尔文(1809-1882)说的,“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51]“还原历史”,主要是运用“大数据思维”(基于大数据的全样思维、容错思维和相关思维)从能动司法视角对已有历史材料进行“重述”,亦即“整理事实”。尽管从哲学(例如现象学、解释学等)的角度讲,“描述的法律史”只能接近“存在的法律史”,但我们主观上仍以还原“存在的法律史”为目标。“升华意义”,主要是运用普世标准对传统中国能动司法进行“重释”,争取“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2016)曾说:“一个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52]我们不是思想家,但我们的思想可以朝着“上升到一般性层面”“赋予普世性的意义”这些方向去努力。
传统中国的“能动司法”,源远流长,化身千万。本书的研究,大致属于“站在巨人肩膀上”,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那种“接着说”的性质。
为了能使本书“惠及”司法实务界,本书没有刻意省略那些在法律史专家们看来是“常识”,但省略它们则影响实务人士完整理解的内容,以致可能说了一些“正确的废话”。本书的研究应该说既有学术视野,又有现实情怀,其认知结果即使不能被接受,但希望能被读懂。
本著是作者主持的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传统中国的能动司法模式研究——以“小事闹大”诉告的司法应对策略为重心》(项目批准号11YJA820004,结项证书编号2016JXZ290)的最终成果,同时也是作者主持的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安全视角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研究》(批准号15BZZ088)的阶段成果。“社会安全”“社会和谐”“情理法”“社会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以及“官批民调”“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等内容,是上述两个课题交叉重叠的重要问题,本著均予以浓墨重彩、深度论述。
本著研究所在的教育部课题,从立项到现在已近八年,这期间对结项成果的修改并不顺利。首先是本人身体出现了一点意外:2017年初我扭伤脚踝,手术四小时、卧床三个月、跛行近半年。其次是书稿修改本身有些“折腾”。原来结项成果书稿的主体内容是传统中国“细事”案(民事性案件)能动司法,修改过程中我将一直在思考的传统“重情”案(刑事性案件)司法能动内容(这个问题的“问题意识”更强)加进来,重新调整书稿结构,将全部内容分为四编:“理论与基础”编、“‘细事’司法”编、“‘重情’司法”编、“总结与传承”编,并以此方案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但随着脚伤的耽误、要求出版的时间大限将到,以及考虑到偏离课题内容太多可能有所不妥,于是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在最初的“结项成果”稿基础上修改完善出版稿,这样一来,时间就显得非常仓促了。尽管如此,本人仍本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心态夜以继日地认真加以修改。
一直以来,国内有一种思潮,认为重视传统就是要回到过去,研究西方就是要全盘西化,我们认为这类认识如果不是肤浅或愚蠢,那就是别有用心!事实上,我们研究历史、了解西方的目的,主要是要弘扬优良本土传统文化、借鉴优良外域资源,同时认清或回答这样一类问题:为什么中国和西方在过去各自是那样的一种政法制度?我们今天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从古今和中西对比考察研究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上述制度不同与各自的地理环境、经济形式、社会生态、文化传统等诸多客观因素有直接关系,其原理大致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我们越了解历史,越研究西方,我们就越应该知道在经济工商化和全球化,社会公民化和生人化的今天,中国当代政法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方向与目标在哪里。本著的研究正是这类思考和表达的一部分。
回望过去,本人自2004年在导师范忠信教授指导下开始系统研究纠纷解决机制问题以来,已经出版的书中有几本似乎可以大致成为一个系列,它们是:《地缘社会解纷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传统社会的纠纷预防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祥刑致和:长江流域的公堂与断案》(长江出版社2014年)、《国家与民间解纷联接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如果加上现在这一本和正在撰写中的《基于社会安全的“三调联动”机制研究》(暂定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这些书大致可以成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成果系列。就纠纷解决的主体而言,这里有国家解决、民间(社会)解决、国家与民间联动(共同)解决;就(广义)纠纷解决的内容而言,这里有纠纷的预防、有纠纷的化解;就纠纷解决涉及的区域而言,有地方性的纠纷解决,有全国性的纠纷解决;就纠纷解决涉及的时间而言,有传统的纠纷解决,有现代的纠纷解决。这种“系列”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偶然天成”,岂不幸甚乎?!
本著即将付梓之际,除了首先要感谢为本著研究立项和提供资助的教育部之外,还要特别感谢以下诸位师友:
本课题组成员,他们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春杨教授、北京邮电大学法学院的黄东海副教授、湖北警官学院法律系的易江波副教授、河南大学法学院的张文勇副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的黄晓平博士、武汉市武昌区司法局的朱小贞科长、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城南派出法庭的杨小瑜庭长等学者和专家。这里要特别的提到的是,豪爽侠义、才华横溢的易江波副教授于2015年4月13日不幸因病永别了我们,实可谓“天妒英才,风摧秀木”;“隽才华文何处再,烟波江上伤别离”。江波的成就和风骨,值得我们永远追念!
课题结项成果的五位评审专家,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赵晓耕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的范忠信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柳正权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蔡虹教授和屈永华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特别是本著的策划编辑张琮军教授和责任编辑牛洁颖副编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本书最早的读者,是本书最后的作者。没有他们睿智、精到的高尚劳动,就没有本著的面世。“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业师范忠信教授拨冗作序,勉励有加,更要专门致谢!
非常荣幸本著能纳入张晋藩先生总主编的《法律溯源论丛》出版。《法律溯源论丛》佳作臻萃,本著忝列其中,突出了本著的主题,升华了本著的境界。
能动司法问题涉及司法、立法等多个领域的理论与实务,传统能动司法问题通贯古今、融汇中外,本人学识未逮、心余力绌,敬祈方家、读者批评指教!
陈会林
2019年4月2日
[①]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一版序言”,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5版。
[②][美]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④] 参见王亚新:“关于滋贺秀三论文的解说”,载[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编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8—99页。
[⑤]一直以来,中西法制传统比较研究的主流思想中有夸大差异性、忽视共同性的倾向。比如,宪法的观念和制度,苏亦工教授指出:毋庸否认,中国是一个缺乏宪政传统的国家,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人毫无类似近代西方的宪法观念。只不过,这种观念比较原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罢了。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中自发地生长出一种中国独有的“约法”观念。这种观念在民间长期流传,但极少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所谓“约法”观念,是指统治者向民众作出的一种承诺,理论上对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约束力。通常在新王朝伊始,某些开国皇帝会向民众作出若干许诺以换取民众对新王朝的支持和臣服。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汉高祖初入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唐高祖与民“约法十二条”。辛亥革命后诞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称作“约法”而不称“宪法”,显然也是刻意要表达这种传统的政府与民众“约法”的观念,以强调其对政府自身的约束力。仔细品味这一传统观念,我们可能会觉得与其说它近似西方的宪法观念,不如说更近似于一种契约观念。其实,西方的宪法观念与契约观念原本就是同源,近代欧洲宪法观念的成长曾经受到社会契约论的强烈影响。在西方人看来,“宪法不过是人民与政府间的契约而已,而契约就是蒈通人之间的宪法。”由此看来,中西传统宪法观念并非毫无共通之处。参见苏亦工:《中法西用——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在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6页;顾元:《衡平司法与中国传统法律秩序——兼与英国衡平法相比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⑥][美]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⑦]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9页。
[⑧]本段所有引文参见范忠信等编校:《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陈顾远法律史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8页。
[1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导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
[12]参见王志强:《<名公书判清明集>法律思想初探》,载叶孝信、郭建主编:《中国法律史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487页。
[13]东汉文学家、经学家赵岐(108-201)在《孟子注疏·离娄上》中说:“(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赵岐注:“权者,反经而善者也。……夫权之为道,所以济变事也,有时乎然,有时乎不然,反经而善,是谓权道也。故权云为量,或轻或重,随物而变者也。”(赵岐:《孟子注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
[14]南朝儒家学者、经学家皇侃(488-545)在《论语义疏》中说:“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皇侃义疏:“权者,反常而合于道者也。自非通变达理,则所不能。……故王弼曰:‘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预设,最至难者也。’”(皇侃:《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1页)
[15]转引自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
[17]现在很多与传统中国“能动司法”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顾元教授的《衡平司法与中国传统法律秩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军平博士的《中国传统诉讼之“情判”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都是将传统中国民事性司法、刑事性司法中的“衡平”“情判”等能动司法情形进行一体考察或研究的。
[18]黄宗智:《中国法律:历史与现实丛书·总序》,见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0]邹韬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载
[21]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22][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页。
[24]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230页。
[25]2018年3月27日梁治平教授在我校做“寻觅‘民法’的踪迹”的学术报告,我被主办方安排为“与谈人”(实在是愧不敢当),在“法律东方主义”问题上受到梁教授诸多指教;2018年11月2日魏磊杰教授在我校所做的“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法治’话语的祛魅与重塑”的讲座,我怀着“听真神讲真经”的心情聆听,受益不少。
[26]Edward W.Said.Orientalism.Pantheon Books,1978.中译本有《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
[27]Teemu Ruskola.Legal Orientalism: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Modern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中译本有《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化》,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9]作者在最后的“结语”(第六章)中提出了“法律东方主义抑或东方法律主义”的问题。参见[美]络德睦著:《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化》,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234页。
[30][美]络德睦著:《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化》,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31]参见梁治平:《有法与无法》,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10月9日。
[32][美]络德睦著:《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化》,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
[33][美]络德睦著:《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化》,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
[36]参见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载《读书》1993年第9期。
[39]Oliver Wendell Holmes,Jr.,The Common Law,Little,Brown,and Company,1948,p.2.转引自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238页。
[40][美]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41]黄源盛:《从无夫奸到通奸的除罪化一以晚清民国刑法为例》,载《甘添贵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下册),甘添贵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2002年出版,第104页。
[42][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载载《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3期。
[43]参见梁治平:《有法与无法》,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10月9日。
[44]魏磊杰:《从“法律东方主义”转向“东方法律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3日。
[45][德]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录》,程代熙、张惠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46] 顾元著:《衡平司法与中国传统法律秩序——兼与英国衡平法相比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7] 刘军平著:《中国传统诉讼之”情判“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8]范忠信等著:《情理法与中国人》,北京大学2011年第2版。
[49]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2版。
[50]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Booth)商学院Christopher Barlow(巴罗)教授提出的一个创新理念。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9dc9b0102zbsr.html,2018年10月5日访问。
[51] 转引自赵旭东:《纠纷与纠纷解决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自序”。


